銀行法案件
工程爭議案件
民事案件
刑事案件
家事案件
實務見解蒐整
證據能力_關於M化車之證據能力
2023-1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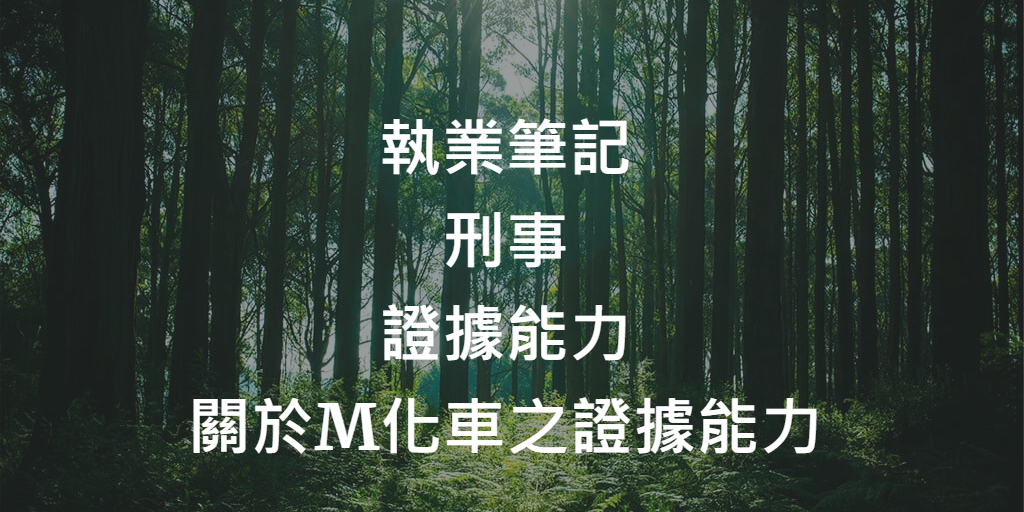 一、懶人包:
一、懶人包:所謂「M化車」是指「M化偵查網路系統」,以車輛搭載虛擬基地台,可以根據手機門號IMSI(SIM卡識別碼)、IMEI(手機序號),進行三角定位,精確測出該門號發話位址,找出罪犯實際所在地點。
目前有高等法院判決見解認為警方使用「M化車」偵測目標手機位置所取得之直接證據,欠缺法律授權,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違反法定程序,並無證據能力。
二、相關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項:「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
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
三、實務見解:
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上更一字第42號刑事判決:
(一) 「M化車」之作用:
「M化車」在偵辦案件的運用上,係使功率可達範圍內之手機將其視為一虛擬基地台,藉此令手機向其註冊,並同時截取IMEI(手機序號)、IMSI(國際標準識別碼)等資訊後再釋放回正常基地台,惟該截取資訊僅為系統自行識別使用,並無可供查詢之門號資訊,亦無法連結辨識第三人資料。而運用「M化車」辦案,係由偵查人員將已知之手機系統識別資訊(如IMSI及IMEI)輸入系統內建立名單,由系統於偵搜範圍內比對過濾出已知目標手機後,再由系統與目標手機連線,並依連線訊號強弱判定手機位置,另第三人註冊於系統內之識別資訊於系統關閉後即自動清除。警方使用「M化車」進行偵查時,皆係依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訂定之「執行M化定位勤務作業流程」辦理。
(二) 「M化車」取得之直接證據,無證據能力:
「M化車」係利用「虛擬基地台」的方式,透過已知的IMEI或IMSI,藉「M化車」與目標設備之間的訊號連結,進而定位目標設備,藉此定位所欲偵查之對象。該定位科技方法,係藉訊號之強弱連結以探知資訊,其實際發動之時間乃取決於偵查機關,且不分目標係在何處(私人住宅或公開場所)而有異,因而導致目標設備、對象所在之位置資訊,不限時間、地點,均得由偵查機關透過「M化車」之使用,持續達到定位追蹤以及蒐集、處理與利用該等資料之目的。偵查機關為追訴犯罪,所為干預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之蒐集,保全犯罪證據之作為,依強制處分法定原則,須法律或法律授權。本件偵查機關使用「M化車」在目標對象即手機持用人不知情之狀態下,秘密蒐集、處理截取手機識別碼位置資料,對目標對象之手機定位、追蹤,以精確掌握手機持用者之所在位置之偵查作為,屬干預人民隱私權及資料自主權之強制偵查作為。而我國目前尚未制定科技偵查法,致偵查機關不足以因應犯罪者利用現代科技工具,衍生之新型犯罪型態。是關於警方使用「M化車」偵測目標手機位置所取得之直接證據,欠缺法律授權,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違反法定程序,並無證據能力。
四、律師解析:
依據上開高等法院判決見解,係認我國目前尚未制定科技偵查法,導致偵查機關欠缺法律授權,不足以因應犯罪者利用現代科技工具,衍生之新型犯罪型態。因此,有待立法機關積極制定相關科技偵查法規,以求人權保障及犯罪偵防之平衡。
此外,值得留意者,係此案所衍生民事損害賠償訴訟,民事庭則認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能力並未設有規定,就刑事訴訟中經被認定不具證據能力之證據,究竟有無證據能力,應從誠信原則、正當程序原則、憲法權利之保障、侵害法益之輕重、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及比例原則,加以衡量其違法取得之證據有無證據能力。因此,仍依相關證據認定被告有賠償責任。
參見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字第372號民事判決:「刑事判決所認定之事實,於獨立之民事訴訟無拘束力,民事法院就當事人主張之事實及其聲明之證據,仍應自行調查斟酌,決定取捨。再按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能力並未設有規定,就刑事訴訟中經被認定不具證據能力之證據,究竟有無證據能力,應從誠信原則、正當程序原則、憲法權利之保障、侵害法益之輕重、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及比例原則,加以衡量其違法取得之證據有無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46號判決、110年度台上字第1103號裁定意旨參照)」、「該詐欺恐嚇集團利用以不斷更換人頭申辦手機門號、輾轉領取贓款之方式逃避檢警追緝,被害人不易舉證;M化車乃警方利用目標手機功率可達範圍內視為一虛擬基地台,藉令手機向其註冊,以截取手機序號、國際標準識別碼等資訊供系統識別使用;且第三人註冊僅供系統自行識別使用,並無可供查詢之門號資料,於系統內之識別資訊於系統關閉後即自動清除等科技特性,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函文可稽(見易字第164號卷㈤第27頁),以輔助與目標手機連線訊號強弱追緝詐欺恐嚇集團成員所在之特定場所,並無顯示具體對話內容、私密場所行為或其他足資識別之個人資料,且經警察以其職務上經驗,觀察系爭處所尚有多人聚集出入、以監視器監看等相當資訊研判可疑為犯罪集團處所(見他字3660號卷㈠第57至58頁蒐證照片),經搜索後扣得犯罪集團使用之被害人年籍資料名單,難認有對特定對象之隱私侵害過鉅或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能力之要求兼有抑制國家公權力行使,以免過度侵害人權,與民事訴訟法上對權衡私人間法益之侵害、真實發現、訴訟促進之要求不同,依前揭說明,並無作相同解釋之必要,是被上訴人抗辯警察使用M化車違法搜證取得之證據均不具證據能力云云,並無可採」、「本院111年度重上更一字第42號刑事判決以:上訴人與其餘被害人遭恐嚇取財時通聯之基地台位址僅係附近一定範圍,無法特定為系爭處所,及於104年6月9日搜索扣得之年籍資料名單,屬易隨身攜帶、移轉之物,已與犯罪日期間隔20日,難認系爭處所為實施本件恐嚇取財行為時之機房;且於系爭處所出入之人除被上訴人4人外,尚有諸多人前往,魏○良自104年5月15日起曾住院,並將手機交曾○榆帶回家而未親自使用,其使用之手機門號雖於案發時出現在前述3基地台位置等情,亦無法達到確信魏○良、曾○榆為本件恐嚇取財下手實施之行為人,而判決渠等無罪(詳見刑事判決理由參、三、㈢、⒈⑴⑵⑶、⒉⑶⑷、肆),依前揭說明,乃刑事共同正犯與民事共同侵權行為之構成要件不同、舉證責任及證明力不同,刑事被告受無罪推定,而民事當事人未為真實完全之陳述仍可斟酌作為全辯論意旨之一部分,為其不利之判斷。是本件魏○良、曾○榆所涉犯罪,雖經上開刑事判決無罪確定,亦無從為其有利之認定」。

